
姓名:干建农 总版主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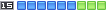
户籍地址: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 积分:22946
最近:18-08-04
|
发表:2009-02-28 17:40:52 人气:521 回复:1   
|
楼主 |
泛滥而有所归-----个人阅读史
干春松
前两天南方周末的一位编辑让我写一篇自己读书经过的文章,虽然,于我来说,这多少有些“无功受禄”的意味,但是作为读书人,还是很愿意跟人念叨自己的阅读史。但是写完之后,发给编辑,似乎不尽符合他们意图,因此只好另写一篇,而这篇经一两个人看了之后,觉得不错,所以将之先放在博客上。新写的那篇等发表之后再贴上来。
泛滥而有所归
前一阵有一个朋友问我,什么时候读书最快乐?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。
如果把“读书”理解成“上学”,那么最快乐的当然是小学阶段。我的小学阶段是在极为轻松的状态下度过的,上世纪的70年代,整个教育秩序还处于一种调整阶段,课程很少,我的印象中文化课只有语文、算术和常识,还有音乐、图画和体育课。作业几乎没有,即使有也必定能在课堂上完成。
那时侯,我们学校门前的溪水还很清澈,可以看见那些小鱼在水里敏捷地游动。夏日的课后,最有兴味的活动就是与班里的几个玩伴下水摸鱼。所谓“摸鱼”就是把手伸到河岸的石头缝隙中去捉藏在里面的小鱼。因为每次能捉到的鱼都不够喂猫的,所以这一活动是一十足的“游戏”。学校后面是一座小山,山上有茂密的竹林,不下河的日子就上山,爬到竹子上,将竹子弯曲到地上,便是一个惊险的秋千。唯一的不足就是蚊子过多。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课外书读。我印象中只有一本《杨家将》的插图本,书的封面已经没有了,但是有杨宗保和穆桂英和焦赞、孟良的插图,没完没了地看。
但如果把读书理解成“阅读”,那么最快乐的则是本科和硕士阶段。我1983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就读,1990年硕士毕业,正值现在被广泛谈论的“八十年代”。那时侯的中国知识分子,有一种“想像的力量”,在经历了长期禁锢的年代之后,他们的激情和能量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那个时候,对一切都感到新鲜,面对一波又一波的西方思想的传入,我们几乎是“随波逐流”,绝对是先接受,后理解。当时西方思想的原著被翻译的比较少,很多的作品只能有一些片断的翻译。比如存在主义,我主要是通过一本柳鸣久先生的《萨特研究》来了解的。后来情况有所好转,弗洛依德热的时候,我们便能看到《精神分析引论》,翻印的《梦的解析》。但自我、超我和本我这些复杂的分析,对于青春萌动的我们来说,远没有“俄狄普斯”杀父娶母的分析来得刺激,当然,对于朋友的梦境的“解析”,更是兴味无穷。最往后的法兰克福学派,我们似乎有了更多不错的译本,《单向度的人》等成为哲学系男生床头的必备。
当时比较流行的是丛书,比如以翻译为主的商务的“汉译世界名著”、三联的“文化、中国与世界”,还有以介绍科学和社会思想为主的“走向未来”丛书,还有一些被翻印出来的新儒家的著作。《悲剧的诞生》、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》还有介绍“系统论”等思想的书籍便是这些丛书中最为引我眼球的作品。当时我最羡慕的是本班有一个同学,几乎把汉译名著都买全了,红红绿绿的摆了一床,但我估计已经经商的他至今也没读完一本。
小说当然也没少读,武侠当然不在话下,而王朔和昆德拉则直接影响到我的思考和口语风格。
或许是受“文化热”的影响,我后来的兴趣逐渐转向中国思想,那时候人们爱讨论的是“传统文化与现代化”的话题,流行很广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难以生发出现代化,而韦伯的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似乎成为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。这种观点的极端化就是后来影响更为深远的《河殇》。而1986年杜维明已经在北京大学开设《儒家伦理》的课程,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被解释为“儒家文化圈”的奇迹,因此,儒家的意义得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。就我个人而言,那个时候最重要的读物是李泽厚的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,里面的《孔子再评价》、《庄玄禅漫述》是我最喜欢的两篇。李泽厚的文采和揭示问题的能力,至今仍是我最佩服的,通过转述他的“瞬息永恒”的禅宗意境,我收获了我的爱情。
1990年之后,我辗转北京外国语大学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、中国人民大学,做老师和编杂志,开始了职业性的阅读和写作生活,读书便不能完全再由着自己的兴致,而且专业性的工作要求阅读必须符合于特定的研究任务,这样,客观上阅读的范围便越来越窄。
尽管,我从事的名为“哲学”的职业,但我自己对于“哲学”书籍的兴趣却比不上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著作,1995年之后,我逐渐将自己的研究重心确定为儒学。除了一些儒学经典之外,我自己对于那些对儒学进行“哲学”解读的著作始终不甚投契,反而是钟情于余英时(《士与中国文化》)、陈寅恪(《陈寅恪史学论著选集》)和瞿同祖(《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》)等政治史和制度史的著作。1998年有一个机会去华盛顿的天主教大学参加一个读书班,阅读的重点是福柯等人的作品,我对其对于“知识、真理和权力”的互动关系的描述有些感触,便开始探讨儒学背后的制度性问题,从儒家知识的真理化、孔子的圣人化和科举制度等多种角度来研究“儒家的制度化”和“制度的儒家化”问题,并形成了自己对儒学的基本的研究角度。
从去年(2006年)到今年(2007年),我参与哈佛燕京“儒家经典的读书班”,阅读的典籍是郭店出土《五行》和《中庸》,这短短的两个文本的研读,整整用了两个学期,几乎每一个文字,历史上重要的注释都被反复的讨论。这样的阅读当然熟悉经典的基本路径,但是这样的阅读对我来说却是头一次。这种阅读的核心在于“古人到底说了什么?”,“现代人对于这些经典解释的可能性”等等。
一个民族总有一些基本的经典,它们构成了这个民族思维方式和价值倾向,或许经典本身我们已经陌生,但是经过几千年的浸润,经典的内在理路已经转化为文化的基因而代代相传。在全球化时代,这个问题似乎越发的尖锐,这些经典对于我们的意义何在,它们与别的族群的经典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?这或许会成为我阅读的动力。
文章源自: http://www.douban.com/group/topic/1586729/ http://www.douban.com/group/topic/1586729/
|

网易BLOG地址: http://nong0916.blog.163.com http://nong0916.blog.163.com
新浪BLOG地址: http://blog.sina.com.cn/nong0916 http://blog.sina.com.cn/nong0916
—— 宠辱不惊,闲看庭前花开花落;去留无意,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
|
|
